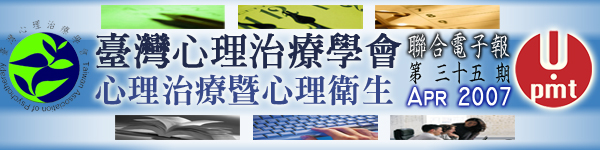第35期電子報專欄:廢墟中的閱讀與書寫>關於片斷的回憶和命題
關於片斷的回憶和命題
誌 Dec 15, 2006
張凱理
抱歉我改了題目,之前訂的題目(Intersubjectivity: How Stolorow et al. read Self Psychology?),我不大想講了,但今天要講的,我不十分確定適不適合當題目,因為有點 personal。先講結論,結論是什麼?結論是講我有兩個角度(perspectives),而第二個角度,其實是回到第一個角度之前,這對我是很有趣的一個人生的意外。
這個題目是今年八月的稿子,起因是因為過去一年半,我有一些寫在部落格的東西,放在一起。回憶的片斷,和關於經驗抒懷明志的命題而已。首先,我的感觸是,心理治療這件事是不可教、不可學、不可做的,特別是精神科,我不曉得心理系狀況如何,我覺得在精神科,這個事情是不可教、不可學、不可做的。現在很多人出來開業,我的看法是,假如你是想做生意,那你應該改行了。把這件事情當成生意來做,實在是我難以接受的。它本質上是 CRAFTSMANSHIP,什麼是 CRAFTSMANSHIP?就是手工藝。就是三峽那個祖師廟,不知道現在弄得怎麼樣了,我大概二十年沒經過那裡,那邊的一樑一龕都是雕出來的,那其實是慢慢雕的,再雕個一百年都不見得能夠完成,但這是恰當的,這跟蓋教堂一樣,應該是多少年的誠意累積在那邊。CRAFTSMANSHIP 為什麼變成絕學?因為這個傳承,基本上是很難傳承的。像蘭嶼的原住民,代代相傳做獨木舟,做獨木舟是把一棵樹砍下來,刨成獨木舟,居然就可以下海抓魚。我以前看過老師傅做木桶,不用螺絲接縫,居然不會漏水,而且可以用很多年,這是很奇怪的。這是 CRAFTSMANSHIP 的本質。
兩個角度就是:(1) THEORIES OF THE SELF AND OBJECT RELATIONS THEORIES, (2)人文精神的憩息之所。這兩個角度花了我二十五年的時間,而第二個角度到這幾年才確定,所以今天這個回憶的分享,personal 的部分或許還是有可以給大家參考的,因為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角度。我以前的想法是,第一個角度會出來得很辛苦,但出來了之後,沒有多久,通常沒辦法停留太久,其實你就陷入了有某個角度之後的框架,那第一個角度通常會限制住自己很多年,有趣的是第二個角度怎麼出來。
第一個角度,就是我一再講的兩個柱子,客體關係理論和自體理論。請注意,這個自體理論我或許起先是講自體心理學,但不會只是在想自體心理學。
而第二個角度,很奇怪,幾年前我講過「人文精神的憩息之所」,這是台灣心理治療學會創會的時候,文醫師找我講個題目,我當時選的題目。所以很奇怪,冥冥之中,我當時選了這個題目。第二個角度,就在迴溯人文傳統,從心理治療來講,這並不抽象,它並不是在清談,它是有方法、有路徑的。明顯的是,它會與存在治療有關。而且既然接到人文,所有人文的書遂都有關,那實在是太好了,那表示這邊的書實在看不完,因為,第一個角度的書,我不否認有學問在裡頭,但基本上,它其實打算只講治療室裡面的事,沒有講到外頭,甚至講到外頭都有點不好意思,覺得好像應該要做一番解釋的樣子,但是如果人文的部份進得來,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唸這些書,而這些書基本上跟人都有關係。那為什麼第二個角度是回到第一個角度之前?因為我覺得我的命格在此,其它的事情都是兜圈子而已。我現在很高興回到了一切開始的地方。
接下來是一些命題。其一是為什麼古典分析理論之後會發展出客體關係和自體理論,這個演變的原委在哪裡?這是我兩個月前被問到的問題,當時我寫下的一段話是這樣子的,我說這很難答覆,關鍵應該在四字,就是 drive、ego、object、self,這是順著 Fred Pine 的講法,前兩者屬古典理論,後兩者 ORT 理論和自體理論則是解釋架構重心的移轉,這個移轉有幾個 implications。第一是,我們對零到三歲的發展,理解遂更清楚。第二是,不再侷限於 Freud 受限於 biology 的思維。第三是,人的經驗和現象成為我們探討的重心。那我覺得,這是我的看法,遂能接上現象學的傳統,而這個傳統恰好是 Freud 擦身而過,他跟胡塞爾都上過 Brentano 在維也納大學的課,但是他跟胡塞爾開出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出來,所以是擦身而過,因為 Freud 堅持科學的典範,遂錯過了現象學的傳統。第四是,解釋架構重心的移轉並非完全否定古典理論。比如說 drive,它絕對是生命的奧秘所在,它是 undercurrent,它是生命的黑潮。地球旋轉天體運行帶動的洋流,那個力量不是人能決定的,大於任何我們已知的力量,那個地方絕對是個奧秘,是生命會動的原因。小池塘沒有波瀾,小池塘沒有東西在流動,大海不是如此。第五是,結構假設還是能夠言之成理,尤其是對於 conflict 為主的精神病理學,但是這個解釋架構的移轉恰可解釋 deficit 為主的精神病理學。
關於兩個理解人的經驗和現象的主軸,為客體關係理論和自體理論,這裡自體理論包括自體心理學,但不是只局限於自體心理學。ORT 的部分,middle school 和 Kohut,精神上是一致的,是講同一件事情。Kleinians 的貢獻則是對黝暗的逼視,這是他們有趣的地方。至於 OR 現象和自體現象遂為一銅板的兩面,這一點,有人可能會說,這個銅板不存在,或這是兩個不同的銅板,或這是銅板的同一面。Whatever,我仍會說這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在這樣的架構下,ego psychology 要怎麼放?Ego psychology 是銅板上面那些細緻的紋路。那怎麼放 drive?怎麼放 id?Id 的部分我覺得是吹一口氣,這銅板遂有生命了,那一口氣拿掉,我可以講,這些東西全都死在那邊。
而過去半世紀裡,諸理論者用不同的概念反覆在講的,都是同一件事,一個人的結構和其界限的穩定度和 viability。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方式在講,比如說,Klein 的 PS ←→ D 理論,Winnicott 的 Transitional object,Michael Balint 的 Basic Fault,和 Ocnophil vs. Philobatism,Benign vs. Malignant Regression 的講法。或 Kohut 的 selfobject 的講法。Minuchin 講家族治療,也在講系統之間的界限的狀態,一個界限有可能是 enmeshed,有可能是 disengaged,有可能是 clear 的。Bowen 的講法其實跟精神分析很像,講 Differentiation of Self,出問題者多在 50 分以下,還算健康的人多在 50 - 75 分,很難有人到 75 分以上,有誰宣稱在 75 以上,我倒想看看他長什麼樣子?比如說,Fairbairn 講的 infantile dependence,到 transitional stage,到 mature dependence,這何嘗不是在講那個 self 形成的狀態和穩定度和隨之而來的客體關係,是如何的演變,但自體分化出來的時候還是有一個 mature dependence,並不是完全就不相干了。或 Mahler 講的 Separation-Individuation,Bowlby 講的 attachment,secure 和 insecure,尤其是 insecure 的部分,而 internal working model 講的是一個人怎麼看待自己、怎麼看待他者、怎麼看待外在的世界,安不安全。可以說,insecure 的,看待的大概都不安全。你看待自己不安全、看待他人不安全、請問這關係要怎麼建立?你看待這世界不安全,請問你要怎麼行走於世間?
所以這些不同的作者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都在講同一件事情,都在講界限上出問題的前因後果,而這些事情,基本上,註定要重演在治療室裡面,因為,當治療者遇到一個界限不穩定的人,你就知道這個相處會有多少困難重演在你跟他的關係中。
講到角度,就要開一個角度的玩笑。這是 Patrick Casement 今年的新書上的一個例子,寫得很可愛。Casement 是屬 middle school 的精神分析師,曾做過觀護人、社工,準備要退休了,這種書我覺得是那種退休之前寫的好看的書。2002 年那本叫做 Learning from our Mistakes: Beyond Dogma in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今年這本叫做 Learning from Life。他說,有一個英國士兵在 Khartoum,Khartoum 是蘇丹的首府,1885 年高登將軍在那裡城圍陣亡,這是英國殖民史上一場慘烈的往事。他們在 Khartoum 幫他立了一個碑,高登將軍騎在馬上。這個英國兵,很崇拜高登將軍,常帶著他的小兒子去欣賞這個雕像。有一天,要移防離開蘇丹了,他們要回英國去了,他跟他兒子說:「我可以答應你任何一個要求,你有想再去一次的地方嗎?」小兒子說:「可不可以再去看高登的雕像?」幾天後,父子一塊站在高登雕像前,沈默的準備跟高登將軍道別,一會,孩子跟父親說:“Dad, who is that man sitting on Gordon? ”孩子只是去看馬的!這是角度有趣的地方,一個人看事情的角度,搞不好另一個人是倒過來看的。所以角度誠然可貴,但憑良心講,也不用太自以為是,非得怎麼樣不可。
精神分析跟動力心理治療,有一個命題是 Fred Pine 說的,這句話是讓我鬆了一口氣的命題,關鍵在「as necessary」、「as possible」,「盡其必要地」、「盡其可能地」。這句話用中文翻過來,叫做盡其必要地做動力心理治療,因為這是盡其可能地作精神分析的前提。
這句話接下來我們會說三遍。
下一個命題呢?這是 Richard Chessick 說的,這個老前輩,學過哲學,他說精神分析跟個別動力心理治療的差別在於,其實動力心理治療是更困難的,治療者常常要換檔,常常要調整自己的狀態,session by session,要根據病人的狀況調整。而精神分析的狀況是,你可以 assume,你可以假設,你可以視為當然,你的被分析者,他的功能、他的穩定度,你可以視為當然。這是因為它已經有一個蠻高的門檻在那邊了,包括它的費用、它所花的大量的時間。一個人如果一個禮拜要進治療室三到四次,你千萬不要以為他是住在治療室的隔壁,他的往返時間,搞不好要一兩小時。台北的交通,你從任何一個點到另一個點,一小時剛好是從容,你往返要花兩小時,加上在治療室裡 50 分鐘,就是去掉半天的時間,有誰有這樣的 luxury?有這樣的奢侈,可以付得起這樣的費用和時間?因為等於要去四個半天!而且精神分析是經年累月在做的,所以,這事情能夠成立的時候,我不管你在治療室裡講了多少瘋話,多少奇怪的 fantasy,好歹你走出治療室,我明天還會看到你,而且你還會付費,那個付費表示什麼?表示一個月要付四萬台幣,一次兩千五,一個禮拜四次的話,有誰有這個 luxury?這個絕對不是拿來付房租和任何其它生活必要開銷的錢。所以這個門檻卡在這邊的話,就等於是已經假設被治療者的狀態,已經不用去管他在治療室外面的狀態,他在治療室外有多大的困難,都可以不用去管他,假如他可以這樣和你一起工作的話。而動力心理治療原則上門檻比這個來得低,以致於我們有可能會收到很亂的病人,比如那些會界限不清楚的病人,這其實很容易發生。
接下來是那句話的第二遍,關於動力心理治療和支持性心理治療,我們盡其必要地做支持性心理治療,因為它是盡其可能地做動力心理治療的前提。能這樣講,我就覺得很愉快了。這表示我們其實可以很放心的做支持性心理治療,千萬不要以為你在做的是沒有必要或價值或錯誤的事情,因為這件事情是在為一件更抽象的事情的可能性做準備。
為什麼要講精神分析?我這幾年來給自己三個理由,我很希望聽到第四個理由,希望這邊有些討論。第一個理由是,精神分析是現代性的產物,而現代性的關鍵是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間有一個辯證在,理性越發達,非理性的反撲就越強烈。這個理性是指工具理性。我不確定我們這個年頭,除了工具理性,還有沒有別的理性?假如有的話,我很樂意知道那是怎麼樣的理性?前幾年我會說,那叫做價值理性,但其實我並不曉得什麼叫做價值理性,我希望能弄清楚。但是工具理性我們是比較熟悉的,就是那個讓我們能夠生活下去的、火車幾點鐘開、捷運幾分鐘一班、不會誤點的東西,那個東西叫做工具理性。第二個理由是,在四百多種個別治療學派中,精神分析是最人文的,原因是因為,它守著那些語言和文字,它沒有辦法很快的變成一個架構,或者很清楚的模型,它漏洞很多,而那個漏洞給它帶來的是,它遂可以繼續再胡思亂想下去。但是,難題是我們學習的時候,會卡在文字的海洋出不來。第三個理由是,精神分析是 clinically relevant,為什麼 clinically relevant?因為精神分析是病理學,它的起源是病理學,它最好用的地方還是病理學。Adorno 這句話,「關於精神分析的事情,全都講錯了,除了那個最極端的地方。」它講的最極端的地方是有道理的,雖然它其他地方都講錯了。
讀精神分析的麻煩在哪裡?因為,它的誕生如果是要解答某種現代性的困境的話,這個解答曾幾何時已經變成症狀或問題的一部份。這樣的命運是不是必然?怎麼樣避免這樣的命運?我想,要能夠不被困住,關鍵在要避免成為症狀或問題的結構的一部份。這個回到個別治療也有關係,大家要當心,不要變成 T-CT (Transference-Contertransfrence) 結構的一部份。變成那個結構的一部份時,我們就沒有辦法不被trap住。我知道我會在裡面,但是我又希望我不被 trap 住,大概是這個意思。所以對這個症狀或問題的結構,勉力要維持一個 critical distance and edge,那麼自己要不懈於 critical self-reflection。但不好的消息是,這一切可能都是徒然的,因為我們會疲倦、會想不下去、會讀不下去、會做不下去。所以治療者的狀況堪憂,他遲早會被困住。
而治療者的狀況的另一個堪憂,今年有一本新書,書名叫做 Removing the Mask of Kindness,它是講治療者有一個很糟糕的狀態,叫做 Caretaker Personality Syndrome,就是治療者一心要當助人者,當照顧者,這其中的 trap,它說 it is not always better to give than receive,施不見得永遠比受來得好,being good can go bad,你一昧想照顧,事情可能會 go bad,可能會更糟,然後 the disease to please,如果你是存心要取悅另外一個人,can even be fatal。這本書我覺得每個治療者都應該讀,我覺得我應該讀。
學習治療,我覺得有一個困難的地方,是那個原則,原則如果能把握得住,我覺得致命的錯誤,或者很糟糕的錯誤,就能夠少很多。那原則我這幾年才比較清楚,顯然我曾經不清楚很久。而且治療者的狀態不比被治療者的狀態來得不耐人尋味,我以前會說,治療者要有粗有細,為什麼?因為如果你只有細的話,你很快就會受不了,細的意思是說,你能夠細微的察覺,好像你聽覺的頻道可以聽到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那真的很慘,多少聲音是比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還來得大,於是乎,你可以聽到太多聲音,幾乎不能不聽到聲音。要有粗的原因是因為有些聲音你會聽不到,這個粗很重要,因為治療者不能太纖細。但治療者不能只有粗,他完全沒有細的話,他就沒有辦法察覺。所以治療者在調整自己的狀態,在粗細中間要做調整。而且我覺得他最好要能夠有豪情,他最好像曹操那樣,被打敗的時候還能夠在馬上橫朔賦詩,所以曹操其實是有趣的人。而我說治療者的命運是由軟到硬,這種講法是有語病的,那請問反過來講可不可以?能不能是由硬到軟?這軟硬指的是心腸。反過來講我覺得是講不通的,因為從硬到軟的治療者,我到目前還沒有碰見過,而且如果從硬到軟的話,他一開始就不會做這件事情。所以,治療者的命運似乎是從軟到硬,硬跟剛剛我講的那原則是有關的。治療者的狀態,這幾年我用的四個字是 structure、是 tempo、是 balance、是 integrity,這四個字我現在沒辦法細訴,但這四個字我覺得是治療者要用來修身的,修他自己的身的方法。那被治療者的狀態,一定是 vulnerable 的,這當然沒有問題,但是治療者不要只能看到 vulnerability,要試著去看到他的長處、他的優點,看到他的 strength,看到他的力氣所在。比如說,他假如會畫畫、寫書法,他假如有一個很特別的喜愛,那太好了。他的長處假如我們沒辦法看到的話,是不對的。而且我們要學習體會時間,這件事情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說清楚,我只能說,有的事情需要多少時間,你勉強不得。五年十年,你說很長嗎?原則上講,你捫心自問,五年前的自己、十年前的自己,知不知道自己要五年十年,才能變成今天的自己?我會這麼覺得,五年、十年,一分鐘都少不了,就是須要這麼久。
那整個從精神分析,這邊有一些感觸。就是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二十世紀初,第一代的 Freudians 有這麼多 mavericks,mavericks 是很不馴的,他們很容易變成 wild analysts,發生過這麼多 tragedies,這些 tragedies 在精神分析頭二三十年的歷史有很多例子。但是,那個年頭卻是能量很強的年頭,從精神分析史上來講。為什麼那時候超現實主義會這麼樣擁抱精神分析?為什麼整個二十世紀的 climate of opinion (Auden) 是精神分析?為什麼是這樣子?前兩個禮拜,在某個討論時,我曾說這是末學,這其實是在挖苦。那我們怎麼去唸精神分析?這個事情跟我們有關嗎?我們在台灣到底接上了什麼樣的 modernity?這個末學的講法是個懷舊的講法,意思是說這個事情它最光輝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那我們有什麼?現在流行什麼,我們就立刻有什麼。所以這跟跑去巴黎血拼LV有什麼兩樣?沒有辦法進入我們裡面的,是那個歷史辯證的過程,那中間有一個過程,其實我們接不上那部分,這是很讓人痛苦的地方。我們進場的時間已晚,我們有兩個 nostalgia,一個是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個不是我們自己本身的,是別人已經在nostalgia,我們接回來,血拼回來的。然後,我們有兩個以上的 vulgarities,vulgar 就是粗暴的意思。所有西邊發生過的錯誤,東邊一定要重新再發生,而且是很快速的一再反覆發生。所以要怎麼讀?好吧!先說誰適合讀?要有點病,但不能病太重,跟文字一定要有緣份,否則你接不上,所以必須是 overreader,有他的內在邏輯的,因為你是幾十年的閱讀、幾十年的收藏,幾十年的內在邏輯在決定了你讀了那些書,這個內在邏輯就是我們的生命的內在風景,但是要怎麼讀?只能大量的讀,照自己的內在邏輯,但是這個邏輯會帶自己去到哪裡,我們事先並不知道。你知道接下來五年要讀什麼書嗎?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確定我明天要讀什麼書!這個旅程最有趣的地方,正是我們不知道那個內在邏輯會帶我們去哪裡。所以這是讀精神分析有趣的地方,讀到斷氣為止。至於這樣馬革裹屍,夠不夠維繫一個人意義之所在,我覺得是個有趣的問題。
Anselm Kieffer 是一個德國畫家,1945 年出生,有一幅畫叫 The Book,他畫的畫,常常是在畫歷史,這幅畫是焦灼大地上面的一本書,這本書遲早會被風化掉,事實上看起來已經風化的差不多了。書,我不曉得你們有多少,我不曉得你們手邊有沒有二十年以上的書,我的意思是說你放二十年了,或者你買了一本二手書,二十年以上的書,二手書我覺得在台灣是不被珍惜的,如果你上 http://www.bookfinder.com/ 訂二手書,是很愉快的經驗,因為很便宜,而且常出乎意料的找到。舉個例子,我手邊有一本「追憶似水年華」,那本書是 1920 前後的版本,書頁上,不曉得誰當時讀過而且眉批,還註明了時間,於是乎,八十年後我買到了一本八十年前有人讀過的書,這本書叫做「追憶似水年華」,這本書的趣味正在這裡。其實,書是有生命的,它會給蟲吃掉,它會被風化,它是有生命的,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它跟數位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而文本,好像文字的海洋,沒有辦法,只能跳進去,但只能跳進去,這件事情顯然是個冒險。而且文字是陷阱,不管閱讀也好,書寫也好,文字都是陷阱。那既然是陷阱,為什麼還要跳進去?因為我們除了這個陷阱,除了文字之外,沒有辦法進入那個世界。你把文字拿掉,一個人很天真,一個人可以不識字,他的生命可以還是有趣的,但是那跟文字的世界很遠,會少了一種人文。精神分析註定是要跟文字打交道的。反過來講,我們要當心文字的機括。牟先生在五十自述裡提到,他在山東長大,他的父親其實是在經營有點像現在的快遞公司,這樣的地方人南南北北很多,當時民初應該就是騎馬或是馬車,那是一個很實在的生活,所以他不是書香世家的那種人,那牟先生碰到熊十力先生的時候才從文字的機括脫困,這個要看他自傳裡頭的描述,這我覺得是中國近代哲學史上很有趣的一段,那這個脫困,我覺得是後面他能在文字的世界裡打轉的時候,很奇特的不受困的原因。牟先生的文字是很好的,他的文字有一種不受限於文字的漂亮的地方,文字的機括沒有把他困住。
而在文字的海洋泅泳的的人,應該把自己當成魚,終究無所得的魚。魚求什麼?不要被大魚吃掉,好好過完一生就好,還要求什麼?因為終究無所得,所以就沒有什麼好計較、好算計,也不須要憂傷自憐,這種魚最好的下場,就是被老人與海的老人捕獲,老人說那是我兄弟呢!或伴著 DEEP BLUE 中,沉入越來越藍以至黑藍的海的潛水者,不再浮起。
治療室裡面有所謂「完美的風暴」,其實我無意要強調「完美」這兩個字,重要的是這種風暴,是那種會翻掉船的風暴,包括被治療者自殺了,當然我們也可以包括治療者自殺了,包括被尾隨,包括 Violent attachment,包括治療的失敗,包括 impasse,包括 boundary transgression,嚴重的 transgression,包括治療者被殺死,這些都是真實可能發生的。
而我們的被治療者其實在講這兩句話「還我一個童年」、「給我一個生活」,他跟治療者這樣吶喊,「還我」、「給我」,但治療者是誰?治療者能還別人什麼?治療者能給別人什麼?你不要說你收了他的錢,我收了你的治療費用,那你要我還你給你什麼?我聽過這樣的笑話,治療者把治療費用還給被治療者,那大概也算是種還。
治療室兩個 dimensions,一個是客體關係的情結,一個是自體的發展。客體關係的情結,帶來的困難是,被治療者一直在繞圈子,他一直在他的情結中繞圈子,一直在 repetition,搞得他的 self 不夠力氣了,他花太多力氣繞圈子了,他的生命沒辦法是直線,他一直在兜圈子,他像是在高雄台北間走高速公路,結果你一直在下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你很快的彎進去一個很奇怪的繞不出來的地方,你沒辦法回到最直接的那兩個點之間的那條線、那條路,所以他們要完成的事情一直都零零落落。他沒有辦法一年、兩年、三年、四年就把它完成。自體的發展要找到一個 leverage for change,但這個 leverage for change 不是治療者給的,是被治療者本來就有的,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self,那些他的長處,那些他的過去的生命學習,那我們能做的就是只能從原來斷裂的地方,把它接上,因為重新再學,從零開始學是很困難的事,假如我失業三年,重新接回去再工作的話,一定是找那個三年前放手的工作,重新再接回去。這是常見的狀況,否則就是從零開始,從零開始很痛苦,到了中年你就知道那是多痛苦的事情。而客體關係的情結像是一個是迷宮 (maze),我起先是用 labyrinth 這個字,後來有人告訴我,labyrinth 其實是不會迷路的,像是歐洲有些花園,弄成一個像 labyrinth 的樣子,奇怪的是,你只要持續往前走,你就會走到出口,但是,maze 不是這樣,它中間有岔路,你走錯路,走到死胡同,轉不出來了,你再繞回來,一再迷路。而 through the maze 時,治療者要維持 reverie 的狀態,這是 Bion 的詞,就是治療者要幫助自己以至被治療者安靜,治療者要盡量不要動。而治療者對被治療者的自體的發展,要 appreciation,要替他高興,當他完成了作品,你要欣賞地說:「哇!這真是一件很好的作品!」,這個 appreciation其實是治療(者)的光明面,他不只是看到病理的部分。
治療這件事情不是繡花,不是那麼纖細的東西,一針一線往返地繡,也不是那種彈琴的時候,一個個音符很怕彈錯的方式的演奏,它是一個不完美的,但基本上是試著要流暢的演奏,而這正是傳統相機和數位相機照相的差別。數周前,一個有陽光的禮拜六下午,V君在照相,他的相機是一個傳統相機,我說你怎麼不用數位相機,他說,用傳統相機的差別是,這是不確定的,可能會失敗、極可能會失敗,沒有辦法複製的,甚至重新洗底片,每一次都會洗出不同結果來,而且有一個物質性的,所以它會泛黃的,所以那個捕捉到的,不可磨滅的瞬間,只能停留在攝影者的腦海中的。當時在陽光下,我高興地說,極可能會失敗,但即使失敗也不要緊的,這就是人文的定義呢。
後來還有一個對話,順著下來,一些聯想,這部分我覺得很有趣,我很期待這部分等一下會有些討論,因為其中有很大的問題。這個對話是關於鏡像的隱喻。一個人照鏡,遂見鏡中的自己。這是 Lacan 所講的 mirror stage,孩子,六到十八個月大,在鏡中看到自己,遂以為他是鏡中的自己。這鏡子是我們一般照鏡之鏡,浴室裡的鏡子。Winnicott 和 Kohut 的鏡子可不是這樣的鏡子,他們的鏡子是父母親的眼神,那個高興的、喜悅的眼神,這個 mirroring 不是那個沒有生命的、只有物理性的東西。如果治療者和被治療者,都為鏡,那他們會在雙方的眼神中看到自己,但這個互相的見到,很可能是扭曲的鏡像。如果雙方是互相投射來去,你投射來我投射回去給你,兩個人就卡在兩面鏡子中間,兩面鏡子中間就會變成鏡陣,鏡子的陣,那就沒完沒了了。鏡之所以成為鏡,是玻璃後面有東西阻隔,把光反射回來,那我們引述 Fromm 的話,他在 To Have or To Be? 書中說,他說藍色的玻璃,之所以為藍色,是因為它把藍色以外的其它顏色都吸收進去,遂為藍色的玻璃。To have or to be 跟這個比喻的關係,就在於 It is named not for what it possesses but for what it gives out,我們是什麼,是因為我們放出了,我們沒有佔有什麼,我們才是什麼。如果照這樣講法,治療者沒有辦法全部吸收被治療者的投射,你能夠全部吸收的時候,你就變成黑色了,你光線都不見了,你全部吸收進去的話。但是你沒辦法全部吸收啊!你還是會折一些回去,或者你沒辦法吸收的部分會被看到,所以治療者必然仍會顯現出除了純然的黑以外的顏色。而黑之為黑,是因為所有的光都被吸收了,那人有沒有可能是純然的黑?純然的黑恐怕是永遠沈默的,恐怕不是人的狀況,那治療者就有三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他是那個 Freud 講的 blank screen,那個雪白的,uncontaminated 的,沒有摻染有色東西的銀幕,你映照上來,那我就映照回去給你,那這就是你的,而我還是 blank screen;第二個是隱含扭曲的鏡子;第三個是除了黑色以外的有色的玻璃。或許,我們可能最希望的狀況,就是除了黑色以外的有色的玻璃,但問題是我們是什麼顏色的玻璃。 Frankl 跟 Fromm,他們讓人感動的地方,就是在這件事情上,就是終其一生,他們沒有對生命失去希望,不管他們曾經吸收了多少扭曲的名堂在自己裡頭。那做為一個治療者,我們散發出來的是什麼?我覺得對我們、對我自己是很大的考驗,假如到頭來,還是 cynical,還是 despair,那我說我自己還困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出不來,我希望自己能夠散發出一點陽光下那種讓人明亮的東西,這是我現在還在思索的事情,我不曉得我能散發出來什麼?而如果一個大自然的風景,它安靜地存在那裡,而安靜地存在那裡,表示它對人不要求有回應,你可以對它大喊大叫,但是它還是沒有回應,它還是安靜地在那裡,泰然地在那裡,那治療者的狀態也應該像如此靜謐的山水一樣。這段是關於鏡像的聯想。我會期待等一下聽到在座諸位的想法,因為你們不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樣。
這幅畫是黑色的,這樣看其實看不出來它的色調的差別,這個是 Ad Reinhardt (1913-1967) 的畫,抽象表現主義和極簡主義的畫家,作品是黑色的,他的畫有哲學的意涵,他有寫下關於他的畫的一些思考,可以上網查一下。
我有一個奇怪的經驗,大概是兩年前這個時候,那個秋天我帶小女兒去學畫,仁愛路上有個青少年活動中心你們知道嗎?我送她去,那時她小六,我送她去,都在樓下走來走去等她,等她下課的時候再接她回家。沒多久,一兩個月後,她就叫我說,你不要陪我了,我說那我要不要來接妳,她說不要接了,她自己搭捷運回來,那是一個有趣的學習,她在學習離家和回家。我那時在附近走來走去,碰到一個廟叫慈恩宮,一個小廟,那個廟很有趣,供的是一個清朝時來台灣的將軍,廟門口橫軸寫著「輕舟一帆下閩南」,一個四十歲上下,看起來有點像智障的人,守廟守得很虔誠,他說這個廟會感應。然後我在廟那邊坐,一坐就兩三個小時,印象中,2004年我正好在準備一個題目,要講 Klein,我第一次講 Klein 的 outline 就是在那裡寫出來的,有一個早上,我在那邊快速的閱讀,快速的概念出來,想我要講什麼,心裡很平靜。為什麼坐在那個地方會平靜?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坐在那個廟門口心會平靜?那個廟在路邊,不是獨立的建築,是在尋常巷子的尋常兩戶人家中間。是因為佛樂,禮佛的音樂?因為佛樂就像海潮一般的重複、重複、再重複?還是因為沈默的神佛?這種平靜是人沒有辦法帶給人的,為什麼那裡會給我帶來平靜?這個限制,我覺得是治療室裡的限制,治療室沒有辦法給人帶來,像一個廟給人帶來的那種平靜。但是,我後來又想,假如沒有那個廟祝在那邊,會有什麼差別?所以我最後的命題是,平靜是來自,沈默的神佛,和虔敬平凡不發問的人。
我剛剛講說第二個角度跟人文有關,抱歉我再講十分鐘,把關於存在治療的筆記講完。存在治療我大概看了十年,到了去年我第一次把 powerpoint 做出來的時候,我才知道這個事情終於告一段落。存在治療的作者,在台灣我們目前所聞大概是 Frankl 和 Yalom,其他作者很少提到。但存在治療其實有近百年的歷史,跟精神分析是並行的。它是源自歐陸哲學,尤其是現象學、存在哲學和詮釋學的一個治療傳統。對於心理治療的眾多學派而言,它是一個小傳統,英國的 SEA(Society of Existential Analysis),會員大概只有 400 多人。但它是最不受限於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思維,也是最親近人文學科的治療取向,這個是關鍵。它的治療精神,是現象學的方法、詮釋學的經驗、和存有的關懷。它的意義特別是在生命轉彎的地方,日復一日、無以為繼之際,一個人如何面對做一個人的腳跟下大事,這是存在治療的意義得以彰顯之所在。
存在治療要從 Ludwig Binswanger 講起,他是 Freud 的朋友,不只是他的學生,是他的朋友。他起先順著海德格的哲學,開啟了 Daseinsanalyse。到了1947年,Medard Boss 開始問學於海德格,結晶於 Zollikon Seminars,有十年的時間 (1959 - 1969) 在瑞士的 Zollikon,一個學期大概去三次,每一次停留兩週,每一週有兩個 sessions。第三心理學 Humanistic Psychology,跟這個有關,Frankl 的 Logotherapy 和這個有關,Laing 講的和這個有關。近二十年,1988 年開始,英國的存在治療學會開創,創立人是一個荷蘭籍的女性叫做 Emmy Van-Deurzen,重要的作者還包括 Ernesto Spinelli,Hans Cohn等,還有就是 Existential Therapies 的作者 Mick Cooper,我的推薦是唸 Mick Cooper 的書,這本書把存在治療到目前為止的情況鋪陳的很清楚。
那我們該如何度量治療室裡的時間呢?最簡單的方法大概是鐘錶罷。但打開窗戶看看,你就會知道,其實天色在告訴我們時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是放一個檸檬在書架上來算時間。沒有切開的話,切開的話就很快,它從青翠的檸檬,變成一個蒼老的檸檬,要花四個月的時間。度量時間,這是一個方式。
那句話的第三個版本現在可以講了,盡其必要地做動力心理治療,以至於盡其可能地做存在治療,因為動力心理治療是存在治療的前提。為什麼這樣子講?因為存在治療講的是 openness to being,而我們的內在情結恰讓我們 open 不了,衝著這句話,動力心理治療和存在治療就有關係。
關於存在之苦境,我有四個字:疲倦、疏離、怨懟、無意義。可能每個人會有不同的四個字或更多字。
最後,疲倦的治療者,午夜打開的書,當然是人文學,難道半夜你還要繼續看臨床的書嗎?我今天講到這裡。
【本文原為張凱理醫師之演講內容,由陳慈怡小姐整理,張凱理醫師審定】